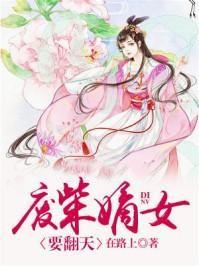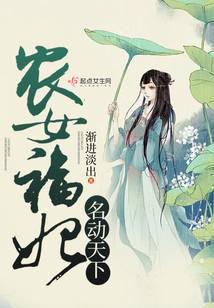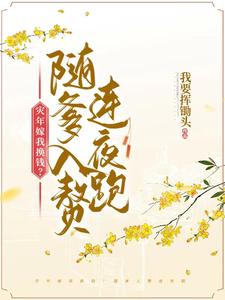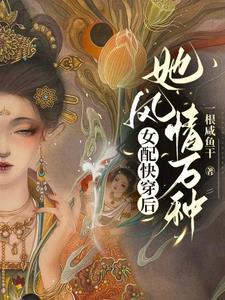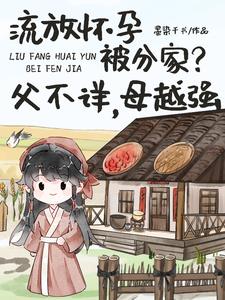第552章 鬥法
王富嬌一如既往的關注點清奇。
方金點點頭:「嬌嬌,到時候,我們就時刻相守,我當了官,每月俸祿都給你買新衣裳。」
「隻是……」
他故意停頓了下。
王富嬌追問:「怎麼了?」
「嬌嬌,若是謀一地縣令,平日還是很忙碌的,縣裡春種夏收,還有城裡百姓的安穩,都得靠縣令,為夫隻怕太忙了,又冷落你。」
眼看王富嬌眉毛一豎,就要發脾氣,方金趕緊往下說。
「但若是謀府城通判,在府城最多算三把手,上面有府尹他們頂著,下面還有差役可用,日子倒是清閑的很,為夫或許能白日偷空帶你去泛舟。」
「至於,監察使,要行走各地公幹,恐怕要夫妻兩地分離,為夫捨不得嬌嬌。」
一番話說完,他將人摟進懷裡。
王富嬌很受用,輕輕捶了下他兇口。
方金悶哼一聲,愣是沒喊疼,依舊目光溫柔的看著她。
「那就通判!通判官大,以後咱孩子也不會受人欺負。」王富嬌摸了摸肚子。
她是被爹嬌養長大的,太知道有個厲害爹的好處。
「為夫也想,隻是,唉,通判要捐十萬兩,為夫哪有這麼多銀錢。」方金心中大喜,面上長籲短嘆。
「怕什麼?我爹有,隻要我去撒嬌一通,爹肯定會給我。」王富嬌驕傲揚起腦袋。
方金一臉為難:「我堂堂男子漢,總是麻煩嶽父,是不是……不太好?」
「那有什麼?我爹就是你爹。」
不得不說,王富嬌是真對方金上了心。
她前幾任夫君,可沒這個待遇,頂多給他們買買衣裳飾品啥的。
「但是,醜話說前頭。夫君,我王家盡心儘力幫扶你,待你得勢那天,要回報的。」王富嬌雙手叉腰,理直氣壯:「第一條,你就算富貴了,這輩子都不能再納妾。第二條,要待我爹比你爹還親。」
方金臉上的表情差點綳不住。
王富嬌善妒就算了,居然還想讓他不孝順。
王老爺出了十萬兩又怎樣,能比的過他爹的一雙手嗎?
他心中怨恨,卻不敢表露,隻哄道:「好!」
甜言蜜語誰都會說,到時候不認賬就好了。
他方金一定會對親爹盡孝,誰都攔不住。
他已經忘了,自從爹回村,他就很少給村裡送東西,逢年過節都不回去的事。
兩人淺淺睡了一個時辰,天就亮了。
兩口子吃過早食,就去了王家。
王老爺早等著了,他聽著傻閨女,把方金許諾的一條條空話說完,依舊面無表情。
若是方金待閨女有兩分真心,或稍微有些品德,他就信了。
他也願意為外孫,一出生就當官家少爺,以後來往都是官宦子弟,出生就站在高位而努力一把。
哪怕是傾家蕩產,但問題,方金不可信。
王老爺一根頭髮絲都信不著他。
「嬌嬌,你可知我們家一年的收益多少?這十萬兩意味著什麼?」王老爺端著茶,擡頭紋都深了些許。
閨女太傻,是他沒教好,他得受著,不能生氣不能生氣。
「爹,我不管那些,您就說幫不幫我?」王富嬌跺跺腳,生氣道:「您要是不幫我,我,我就不吃飯,餓著您外孫您別心疼。」
王老爺:……
他默默咽下一口老皿:「爹沒說不幫,這樣,你先去後院歇歇,我和女婿單獨談談。」
王富嬌不樂意,嘟著嘴都能掛油壺了。
可王老爺就當沒看見,氣氛一時僵持住了。
一進門就當自個隱身的方金知道,他不表態不行了。
「嬌嬌,你聽爹的,去休息會兒,你現在雙身子,可不能累著。」
「好吧。」王富嬌現在是看他正順眼的時候:「那爹,你可別欺負方金。」
說完,她才帶著下人走了。
王老爺是真服氣,這麼多年了,也隻有方金能做到,給他閨女迷成這樣。
明明昨天哭著回來的,還鬧得休夫了。
嘆口氣,他看向方金:「嬌嬌不懂事,你該知道的,方金,十萬兩,恐怕你祖宗八輩加起來,都賺不來這麼多錢吧。」
這話不算羞辱,方家世代貧農,真的窮。
「是,小婿知道此事為難嶽父大人了,可小婿沒辦法,總要為嬌嬌和孩子的以後考慮。」方金微微彎腰,一副真誠的語氣。
「隻要這次小婿翻了身,必然不會忘了您的恩情。小婿會還錢的。」
至於以後怎麼還錢,方金不說,兩人都懂。
俗話說的好,三年清知府,十萬雪花銀。
何況通判,真當上了,他有的是法子撈油水。
「呵,方金,我是商人,見過的人不少。這做生意前,說的天花亂墜沒什麼用,到底怎麼樣,還要看之後。」王老爺把事挑明了,敲打他。
方金一琢磨,就道:「嶽父,我願意寫欠條。」
欠條,那有什麼用?
方金真當了官,有的是法子讓欠條變成廢紙。
「那倒不用,你畢竟是我女婿。」王老爺搖頭:「我要再多的保障,也不過是為了閨女。」
「這樣,你把你名下的宅子、田地,不如過戶到嬌嬌名下?算是給她個底氣。至於縣城的鋪子就不用了,你還有兩個兒子,當爹的,總要為他們考慮一二。」
鋪子捨棄,是他先前答應何氏的。
而在方金看來,王老爺要這些,目的不是產業,而是在警告他。
以後當了官,資源人脈都隻能傾向王富嬌的孩子,至於方澤天他們,用縣裡鋪子打發就夠了。
王老爺是想保障外孫的未來。
不然,他的田地宅子啥,賣了最多值兩千兩左右,怎麼能和十萬兩的欠條相提並論?
對此,方金雖然不滿王老爺的強勢,但還是決定先答應下來。
方澤天他們,有個當官的爹,日子還能過差了?
「小婿明白,今日就去辦過戶,多謝嶽父願意鼎力相助。」
方金彎腰行禮。
王老爺擡手阻止:「哎,急什麼,老夫雖有心幫你,但王家多年積蓄,也不夠十萬兩,隻怕能勉強謀一縣令而已。」